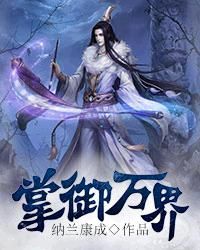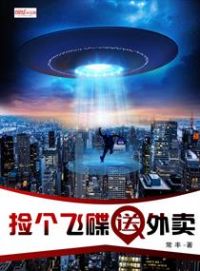在检查死者双手时,张林注意到指甲缝里残留着灰黑色物质。他立即用微量物证刷仔细提取样本,放入真空密封袋:"这些可能是与凶手搏斗时留下的皮屑、纤维或其他物质,需要进行DNA检测和成分分析。"他又转向死者的脚踝,发现两处陈旧性擦伤,伤口边缘已被尸蜡覆盖,但仍能看出外力拖拽的痕迹。
解剖进行到胃部时,张林使用手术剪小心打开胃壁。胃内残留着少量半消化的食物残渣,通过显微镜观察,可见玉米、青菜等植物纤维,以及未完全分解的肉类组织。"根据食物消化程度,结合尸蜡化延缓腐败的特性,"他在记录本上快速书写,"初步推断死亡时间在三年左右。"
在处理头部解剖时,张林特别谨慎。他先用电动骨锯沿颅顶切开,锯片与颅骨摩擦产生的焦糊味混着尸蜡气息,令人作呕。掀开颅盖骨后,脑组织已全部蜡化,呈现出均匀的淡黄色固态。"尸蜡化使脑组织避免了液化分解,"他用解剖刀轻触蜡化的大脑,"虽然失去生物活性,但形态保存完整,或许能为某些病理分析提供依据。"
整个解剖过程持续了近五个小时。张林将提取的数十份组织样本分类编号,包括血液、内脏、骨骼、指甲缝残留物等。每一份样本都可能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:血液中的药物成分检测可以判断死者是否被迷晕,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分析或许能揭示生前生活环境,而指甲缝的DNA对比则可能直接锁定凶手。
当最后一针缝合完毕,张林摘下手套,疲惫地靠在解剖台旁。窗外天色渐亮,解剖室的白炽灯依旧刺眼。他望着记录本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和观察结果,深知这些看似冰冷的解剖结论,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一个消逝的生命和等待揭开的真相。
尸体解剖的结果在第2天早晨的时候就已经放到了李明的办公桌上。
但是并没有太多的线索和发现李明这边已经向市。局秦川那边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相关的案件情况,秦川那边也做出了了解,说实话,施拉化现象的尸体非常少,秦川。在这么多案件当中也是第1次碰到。
而这个案子过去了这么长时间,两三年都过去了,当时报的是失踪过程当中也没有找到李庆民失踪的一些具体线索,现在发现人已经死了。反过来想找凶手,实际上也非常困难,主要还是要从死者的人际关系调查出发。
刑侦支队。
陆川将李庆民的照片钉在白板中央,用红绳串联起云和县与海州市的地图标识,晨光透过刑侦支队的玻璃窗,在照片上投下斜长的阴影。"死者在海州经营建材生意三年,"他的手指划过白板上密密麻麻的便签,"重点查他公司的账目、合作伙伴,还有失踪前三个月的行动轨迹。"
小王带队抵达海州市时,李庆民生前注册的"庆达建材有限公司"早已人去楼空。老旧的写字楼里,前台接待处的玻璃上蒙着厚厚一层灰,墙角堆放的纸箱里,散落着褪色的宣传册和半截发霉的名片。"三年前突然停业,"物业管理员翻着登记册,"水电费都欠了半年,老板电话根本打不通。"
走访李庆民的生意伙伴异常艰难。曾经的供应商陈老板在办公室里反复擦拭紫砂壶,听到"李庆民"三个字,手突然顿住:"早不联系了,他公司资金链断了以后,好多人都被坑了。"当小王追问具体债务纠纷,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:"都过去这么久了,提这些干嘛?"
在李庆民昔日的会计家中,老式风扇吱呀作响,吹得桌上的账本哗哗翻动。"他失踪前确实很反常,"会计推了推老花镜,浑浊的眼睛盯着泛黄的账目,"大量资金莫名其妙转出,问他也不说。有次半夜接到他电话,说话颠三倒四的,好像很害怕......"话音未落,老人突然剧烈咳嗽,再问下去,只摇头说记不清了。
最有希望的线索来自李庆民的司机老周。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坐在小饭馆里,面前的啤酒喝了大半,才终于开口:"出事前半个月,老板总去城西的码头,说是谈生意,可每次都空着手回来。有次我看见他在车里哭,那是我跟了他五年,第一次见他那样......"老周的声音哽咽,却在小王追问具体细节时,突然借口上厕所,再也没回来。
云和县的调查同样陷入僵局。李庆民的老家是栋破旧的二层小楼,院中杂草丛生,邻居们对这个常年在外的"有钱人"印象模糊。"好几年没见他回来了,"隔壁阿婆坐在门槛上纳鞋底,"他爹妈走的时候,都是亲戚帮忙办的后事,唉,赚那么多钱有啥用......"
当专案组试图调取李庆民的银行流水时,发现他名下多个账户在失踪前一周被清空。转账记录显示,大笔资金分散汇入十几个匿名账户,最终流向境外。"这些账户都经过多层包装,"小孙盯着电脑屏幕,眉头拧成疙瘩,"想追踪源头,比登天还难。"
连续两周的走访,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线索,却没有一条能真正指向关键。陆川站在白板前,将所有调查结果梳理成时间轴:资金链断裂、频繁前往码头、异常转账、突然失踪......这些零散的片段如同破碎的拼图,始终无法拼凑出完整的画面。
"再查他的私人社交账号,"陆川突然开口。